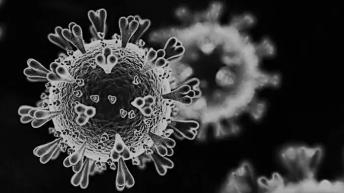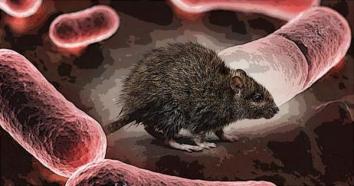倘若你翻开历史,便会发觉人类跟瘟疫的博弈从来就未曾有过平局,每一回大流行不但使生命消逝,而且还会把社会的旧伤疤撕开,将偏见、恐慌以及人性弱点暴露出来,明白这些教训,并非是为了去预测下一场瘟疫什么时候来临,而是为了下一次我们无需再次走上老路。
替罪羊逻辑总在恐慌时最畅销
1348年,黑死病在欧洲蔓延,那时,法国医生阿方索·德·科尔多瓦给出一个“科学”推断,即:鉴于疾病是因中毒所致,那么,除了空气中的毒气外,人也能够主动下毒。这一基于当时医学理论的猜测,直接致使犹太人成为整个欧洲的目标。从西班牙至德意志,成百上千的犹太社区遭焚烧,原因是他们在井中投放毒物。并非宗教狂热,亦非陈年宿怨,而是当时最为前沿的医学知识为屠杀提供了“理性根据”。
新冠疫情这个时期里,距离现今是七百年以后,亚裔于欧美街头被辱骂还遭遇袭击,并且5G基站被人纵火,阴谋论者宣称比尔·盖茨在疫苗当中植入了芯片。手段发生了变化,可逻辑并未改变 —— 面对未知的能带来致命后果的威胁,人类依旧急切地需要一个能够看见的敌人。在特定社会里地位脆弱、形象模糊的是谁,谁就容易在下一场瘟疫之际成为新的“投毒者”。
浪漫化疾病是对逝者最大的不敬
欧洲在19世纪初时,肺结核被包装成了一种“文艺病”,诗人济慈咳血之际写下了“静谧的死亡”,雪莱为病弱的友人进行吟唱,拜伦甚至表明希望死于这种“优雅的消耗”,当时上流社会的女性刻意去追求苍白瘦削从而模仿肺结核患者的体态,不过现实却是在英国单单19世纪中叶肺结核的年死亡率就达到了十万分之三百以上,伦敦贫民窟里挤满了咳血的童工。
实质上这种浪漫化是特权阶级的自我麻醉,富人能够前往海滨进行疗养,依靠牛奶以及新鲜空气来延续生命,然而穷人却只能挤在通风状况恶劣的出租屋内直至死亡,今天我们不会再去美化癌症或者艾滋病,可是仍然存在有人给工作过劳贴上“奋斗”的金粉,通过“燃烧自己”去美化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将疾病与才华、崇高强行联系在一起,最终受益的向来都不是病人。
民间巫术暴露制度缺位时的绝望
18世纪初期的时候,塞尔维亚这儿以及东欧地区之中呢,流行起了“挖心驱魔”这么一种仪式。倘若在一个家庭里面,接连有好些人因为类似肺结核的症状死去,那么幸存者就会去掘开先逝去之人的坟墓,把心脏取出来烧成灰,然后拌到水里或者酒里面,喂给正在生病的家人喝。当地的人相信死去的人会变成吸血鬼回来捕食活着的人,把心脏烧成灰喂药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可不是偏远乡村的孤单例子,类似的驱魔仪式在普鲁士军队占领的区域也有着详细的记录。
在今天听来那是荒谬的,然而在当时并不存在任何公共卫生系统,医生的诊费高到能让普通农户有三个月的口粮作为支撑,死亡率攀升至连神父都不愿意前来主持葬礼的地步。当正规医疗完全处于缺席状态时,哪怕再离奇的巫术都会被视作救命的依靠。眼下我们会嘲笑那些喝消毒水来预防新冠的美国人,也嘲笑那些涂抹大蒜用以防非典的农村大妈,却很少去追问:当他们尝试这些办法之际,正规的信息渠道以及廉价的防护物资究竟身处何方?
疾病的污名比病毒本身更难清除
在1982年,当艾滋病被命名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之际,科学界已然犯下了错误。一直到1984年,病毒分离得以完成之时,医学界方才确认HIV并不区分性取向。然而,此等污名却始终追随着艾滋病直至今日。在1990年代,美国所进行的调查表明,超过30%的民众依旧认定艾滋病是“对同性恋者的天罚”。桑塔纳于《艾滋病及其隐喻》之中提出了去社会化的纯粹生物医学视角,可是这个理想从来都未曾实现,这是由于病毒借助性传播,而性从来都不单单只是生物行为。
在中国,艾滋病早期时,血源性传播致使大量卖血的农民受到感染,这些农民和同性恋没有任何关联,然而他们却依旧承受着相同的歧视。患者被从村庄驱赶出去,子女被学校劝退,在婚恋市场上,人们听闻便面露恐惧。直至今日,公众对于HIV的认知仍旧被三十年前的道德判断所束缚,阻断药的知识普及远远比不上“这是谁的责任”的讨论热烈。
慢性病转型曾让人类误判了胜算
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消灭天花,那时,主流医学界弥漫着乐观情绪,美国卫生局局长甚至在公开演讲里讲“我们可以合上传染病学的书本了”,接下来的二十年,各大医药公司裁撤传染病研发部门,资金涌向抗癌药和心血管药物,没有人想到,1981年首次报告的少数同性恋者肺炎病例,会在二十年后成为全球2700万人的死因。
这种误判所带来的代价是极为巨大的,2003年SARS出现大规模发作的情况时,全球范围内几乎不存在新研制出来的具有广泛抗病毒作用的药物可供使用,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地区失去控制,这是由于疫苗的研发早在十年之前就因为市场前景不太好而被放置搁置起来,我们错误地认为科技的进步是一直朝着前方不回头的态势,然而却忘记了病原体从来都不会遵循人类所制定的时间表。
社会组织的质量决定瘟疫的长度
1918年时,大流感肆虐,费城在尚未出现任何病例的情况下,就举办了发行公债大游行,有二十万市民聚集于此,三天之后,医院就呈现爆满状况,六周的时间里,死亡人数达到一万两千人。同年,圣何塞,市长以及卫生局长在首例确诊之后,立即关闭了学校、剧院还有教堂,死亡人数仅仅是费城的三分之一。这两个城市具备相近的医疗水平,其唯一存在的区别便是决策者是不是尊重公共卫生的基本逻辑。
在2020年年初之时,中国的乡镇干部采用大喇叭喊话的方式,进行封村设卡的举措,还挨户开展摸排工作。这些办法不会被写进任何一本传染病学教科书之中,然而却在武汉之外成功地拖住了病毒扩散的脚步。历史不断反复证明着:在没有疫苗以及特效药的情况下,隔离、信息透明、基层动员能力就是最为强硬的药物。技术会取得进步,药物会进行迭代,但是应对瘟疫的第一道防线始终是能够有效运转的社会系统。
此刻请你回忆一下你所历经的最近一桩公共卫生事件,不管是流感季里医院出现的排队情形,又或是疫苗预约之际系统发生的崩溃状况。你觉得在下一场大流行来临之前,我们最应当即刻补足的短板是哪一项呢?欢迎于评论区分享你的洞察,还请把文章转发给你所关切之人。